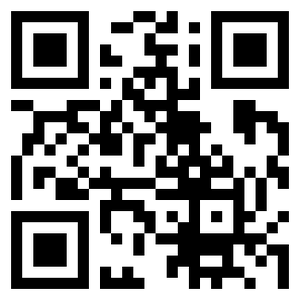“1948年11月13日零六三〇,陈先生还没回电话,怎么办?”陶副官隔着雕花门板低声禀报。清晨的暖炉才刚点着在线炒股配资看必选,浓茶的蒸汽在空中打着旋儿,却怎么也驱不散那股莫名的寒意。
蒋君章坐在走廊尽头,抬腕看表,秒针滴答滴答。他回想着昨夜十点光景,陈布雷把自己关在房里,只交代一句“勿扰”。外面炮声时断时续,宋子文的电报催促着南京、上海两头的筹款,他觉得整座官邸像被一只无形大手攥住,连呼吸都费劲。

八点过五分,值班电话又响起,中央部的秘书催开会。蒋君章替陈布雷请了病假,挂断后却没底气:这位老先生一向守时,即使凌晨批稿,也会在七点半准时用粥。今天太反常。
有意思的是,门缝里一点光都没有。蒋君章突然想起昨天下午陈布雷在阳台晒稿纸时的那句话:“若国事无望,吾等亦无可为。”话音轻,却像把锈钉。

十点整,他按捺不住,示意陶副官从气窗探看。气窗开启,冷风裹挟着残叶钻进来,帐幔垂到床脚,丝毫未动。陶副官喃喃:“似乎不对……”话未落音,蒋君章抬脚撞门,铜锁断裂,室内药味呛鼻。陈布雷仰卧,面色灰黄,床头放着两只空安眠药瓶,一封淡蓝信封压在胸前。
痉挛般的沉默后,两人拨通总统官邸。线路嘶嘶作响,周宏涛在那头只说了两个字:“知悉。”随后数通电话撒向陈方、陶希圣,再拨往上海。王允默听完噩耗,先是一声“啊——”随后便是静默,像是电话线被割断。
车站的汽笛在中午十二时长鸣,王允默与长女陈琏挤上最快的一班急车。车厢里,陈琏攥着父亲去年寄来的《易经》手稿,眼圈通红却强忍不语。母女俩心里清楚,父亲的死决不仅仅是身体衰弱,更是精神的崩折。

同一时间,重庆枇杷山官邸。蒋介石换下戎装,着一身素灰长衫,步速疾快。他对宋美龄低声道:“伯怜二十载为我效命,朕负之。”宋美龄欲劝而止,目送他起车。外人很少见到蒋介石如此神情恍惚。
下午两点半,灵堂暂设总统一号楼侧室。棺木未合,蒋介石俯身端详,像在寻找最后一丝心跳。他的手轻抚棺沿,指尖微抖。随后提笔,浓墨写下四字:“当代完人”。落款处他的“介石”两字几乎看不出力道,仿佛怕惊扰了故人。
为什么要给陈布雷国葬?从军政运作看,国民党内部对失败已心知肚明,亟需一个“持节而死”的典型来稳住军心。更深一层,是蒋介石个人情感:1927年南昌清晨,陈布雷递上《告同志书》草稿,使蒋介石在文宣战先声夺人;1936年西安事变日夜混乱,他独守桌前缮写《宣言》,让外界知道“委员长安好”;抗战八年,数百篇演讲稿出自这支笔。如此文胆,说一句“左右手”都嫌轻。

然而,国葬的提议遭到王允默婉拒。她致电官邸:“先夫素俭,丧事不宜铺张,愿安葬西湖旧地。”蒋介石沉吟良久。对策部原本打算将葬礼抬高至“国民革命烈士”级别,藉此提振士气。宋美龄复述王允默的决意后,他轻轻摆手:“随夫人意,只不可怠慢。”
遗憾的是,外界只见到仪式表面,未见到陈布雷留下的八页遗书。那份手稿里,他痛陈党政腐败、行宪失信、经济失序;他坦言对内战持彻底悲观态度,并以“愧对国人”自裁。陈方后来向媒体透露只一句:“先生以身殉国事”,其余内容密封。
试想一下,一位自幼醉心民族民主的报人,三十年代因“唯蒋可救国”而投身中枢;二十年后,却因“国无可救”而服药,这种巨大落差足以摧毁任何坚强意志。有人说他糊涂,有人说他悲壮,历史却没有给他解释的时间。

临葬当日,灵柩由空运至杭州,停放于九溪梅庄旧地。飞行员特意绕西湖半圈,机腹白花飘洒,如雨纷飞。留守官员在场合念悼词,而游客多不知这位“当代完人”究竟何许人也。山风穿林,几声鸟啼掠过,场面说不出的冷清。
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:“布雷殉难,使我心折。以我失人,岂布雷失我。”同年十二月,他命人在灵前再添一匾,字迹更小,写的是:“清慎勤”。多年后整理档案的史官推测,这或许是蒋对自己在用人失察上的一种补偿——却已于大势无补。

历史的温度常常取决于叙述者。对陈布雷,民间多记得他协助蒋介石,少有人提他北伐时期在《时事公报》痛斥军阀的锐利文章;对蒋介石写“当代完人”,后来也有人讥讽为政治表演。但凡事落到具体人身上,其复杂绝非一句评语能概括。
九溪旧墓至今仍在,石阶青苔湿滑,碑文风化。偶有老游人路过,念两句诗便匆匆离去。墓后竹林深处,埋着一支折断的笔,那是王允默按丈夫遗愿放入棺中的旧物;无声,却有锋芒。
金斧子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